核心观点:
行政登记是登记机构依法对权利归属或其他法定事项加以审查、记载和确认,并向社会宣告和公示的一种行政行为;行政确权则系对权属纠纷予以裁决的行政行为。前者起着官方证明和赋予公信的作用,后者具有授予权利、确定归属的法律效果。颁发林权证的行政登记行为,仅有公示、宣告作用,不具行政确权功能,所涉当事人之间就山林权属存在的争议,应当依法通过调处程序予以解决。

坎头村5组向本院申请再审,请求:撤销一、二审判决,依法再审本案并支持坎头村5组的诉讼请求。事实和理由:(一)坎头村5组提交的1952年泰和县八墈字第1730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和1982年泰和县(泰)林证字第13758号山林所有权证确认的贰拾名山场四至界址一致,所涉林权由坎头村5组享有。案涉142宗林权证的四至范围几乎与坎头村5组的贰拾名山场重叠,导致坎头村5组的贰拾名山场有名无实。(二)新坪村7组、9组及其村民在“林业三定”时期取得的山林所有权证和自留山使用证系伪造,县政府未经勾图和现场勘验,即在林改时期颁发案涉142宗林权证,导致双方土地山林界址不清。县政府作出的复核结果未附四至地形图,不符合《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》第十六条的规定,且县政府未依照坎头村5组第一次提出调处山林权属纠纷的申请作出调处决定书,而是作出复核结果,应当撤销。(三)一、二审判决根据《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》第二十一条规定,以“林业三定”时期颁发的山林所有权证为依据处理县内山林权属争议,适用法律不当。2003年7月17日《林业厅关于山林权属争议调处有关问题的复函》规定,确定山林权属应以土地改革时期确定的权属为基础,以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为主要凭证。在“四固定”、“林业三定”中为方便管理或因体制变化等原因,对山林权属进行调整,必须当事双方签订有关协议,或经乡级以上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,或经人民法院作出判决,在此前提下,山林权属才能变更。因此,如对“四固定”或“林业三定”中颁发的山林权证提出疑义,就应重新审查、核实其颁发的依据。《森林条例》第五十二条也规定,违反法定程序发证、伪造发证依据或者错误发放的山林权属证书,原发证机关应当撤销所发的山林权属证书。坎头村5组具有四至范围一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和山林所有权证,但新坪村7组、9组一直拒绝提供与“林业三定”时期山林所有权证四至一致的权源依据,举证不足。一、二审判决未查清新坪村7组、9组取得山林所有权证的权源依据,有违山林所有权来源于土地所有权的基本原则。(四)一、二审判决未要求县政府提交颁发案涉142宗山林所有权证合法有效的权源依据,对县政府提交的“林业三定”时期四至明显有误的山林所有权证视而不见,并认为该山林所有权证是否伪造应由坎头村5组举证证明,有违行政诉讼法的证据规则。
县政府辩称,其颁证行为程序合法,事实清楚,依据充分;其根据坎头村5组的申请,经审查作出的复核通知,亦无不当。一、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,适用法律正确,请求依法驳回坎头村5组的再审申请。
吉安市政府辩称,其复议行为程序合法,事实清楚,依据充分。一、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,适用法律正确,请求依法驳回坎头村5组的再审申请。
新坪村7组、9组述称,其享有的案涉142宗林权证合法有效。坎头村5组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,依法应予驳回。
本院再审审查期间,县政府提交1953年泰和县(村西村、富溪村)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36份,作为新的证据,拟证明新坪村7组、9组“林业三定”时期的山林所有权证具有上溯至土地改革时期的权源依据。坎头村5组发表质证意见称,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,但对其中载明系村民个人所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的合法性不予认可,上述土地房产所有证与新坪村7组、9组“林业三定”时期的山林所有权证的四至均不一致,亦不认可其关联性。
法院认为:(一)行政登记是登记机构依法对权利归属或其他法定事项加以审查、记载和确认,并向社会宣告和公示的一种行政行为;行政确权则系对权属纠纷予以裁决的行政行为,属行政裁决之列。两者之间具有实质性不同,前者起着官方证明和赋予公信的作用,后者具有授予权利、确定归属的法律效果。对此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十六条、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第二条,以及《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》第十条、第十八条均有相关规定。因此,颁发林权证的行政登记行为,仅有公示、宣告作用,不具行政确权功能,所涉当事人之间就山林权属存在的争议,应当依法通过调处程序予以解决。本案中,坎头村5组因与新坪村7组、9组之间存在山林权属争议,经协商不成,向县政府提出了调处申请。县政府本应依法适用调处程序处理当事人之间的山林权属争议,却仅适用复核程序对案涉142宗林权证的颁证行为进行形式审查,吉安市政府经复议维持县政府的复核结果,均有不当。
(二)《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》第二十一条规定:“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,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。林业三定时期未确定权属的,参照农业合作化、四固定时期确定的权属;农业合作化、四固定时期也未确定权属的,可参照土地改革时期确定的权属,凭当时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或其存根处理;双方都无证据的,人工林的山权、林权均归造林一方所有,天然林或荒山荒地,按山权、林权各半的原则并结合自然地形处理。”本案中,坎头村5组与新坪村7组、9组对案涉林地权属存有争议,且均持有“林业三定”时期的山林所有权证。在此情况下,县政府未上溯审查、核实双方农业合作化、“四固定”时期或土地改革时期的山林权属状况,仅以新坪村7组、9组及其村民“林业三定”时期的山林所有权证作为权源依据,适用法律有误。
(三)根据本案已查明事实,县政府在颁发案涉142宗林权证时,未组织其“南至”接界人签字。县政府虽辩称,若宗地之间有小河、道路等明显地物标、天然地标的,实践中无需接界人签字。但经本院现场勘查,争议界址并无明显地标,县政府的抗辩不符合《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确权发证操作规范》第二十条关于“省、县界大山脊和河流无法了解的,可以不填”的规定。故,县政府未经接界人签字的颁证行为,有违法定程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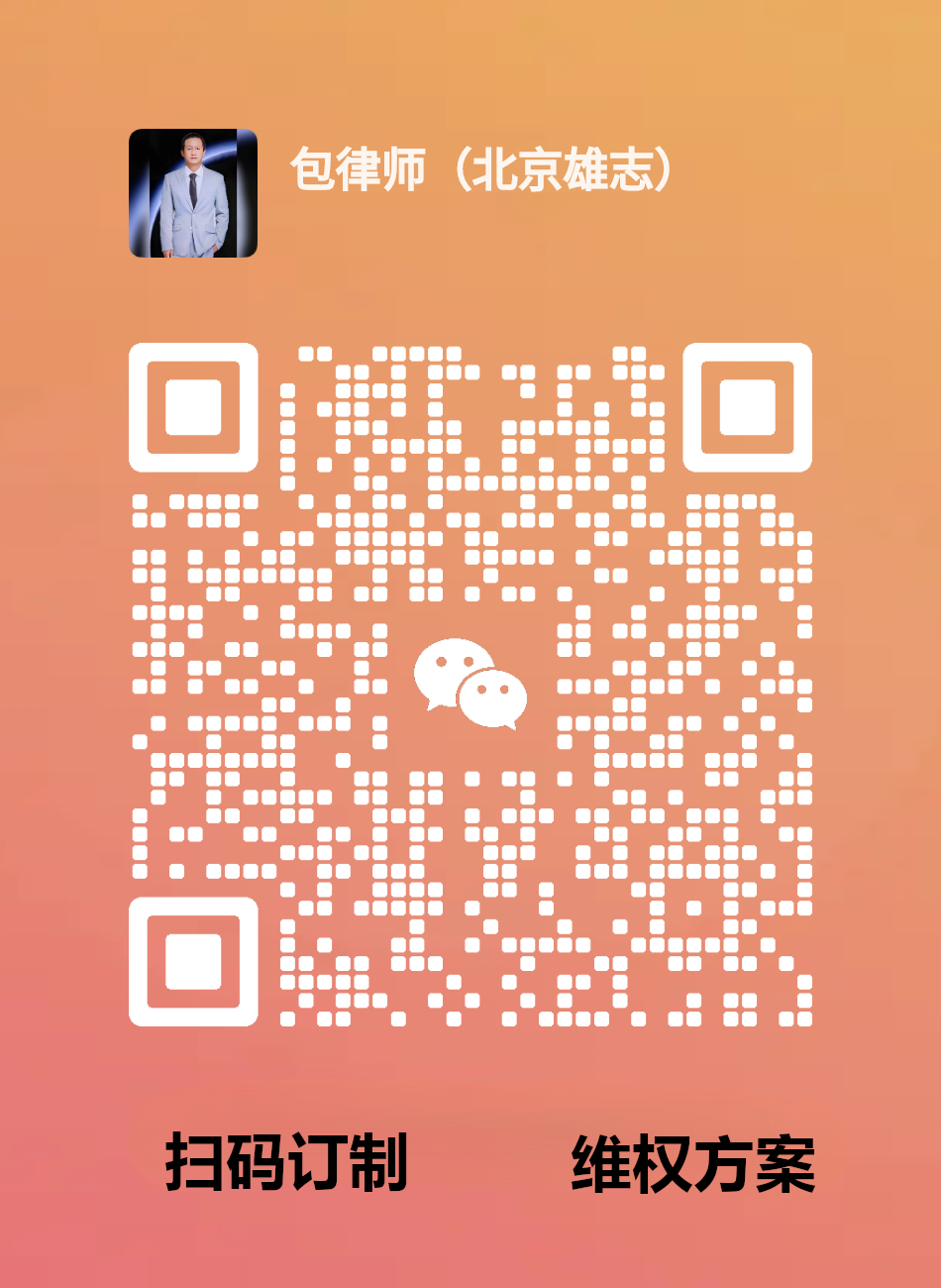
发表评论